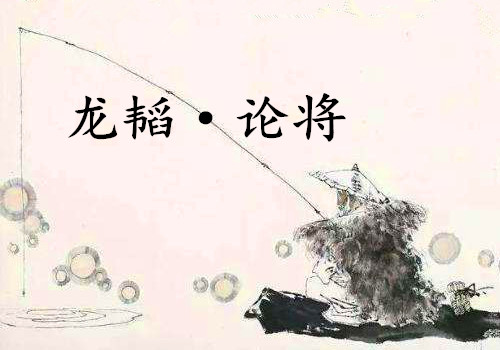陈琳《饮马长城窟行》的文学价值
饮马长城窟行
魏晋:陈琳
饮马长城窟,水寒伤马骨。
往谓长城吏,慎莫稽留太原卒!
官作自有程,举筑谐汝声!
男儿宁当格斗死,何能怫郁筑长城。
长城何连连,连连三千里。
边城多健少,内舍多寡妇。
作书与内舍,便嫁莫留住。
善事新姑嫜,时时念我故夫子!
报书往边地,君今出语一何鄙?
身在祸难中,何为稽留他家子?
生男慎莫举,生女哺用脯。
君独不见长城下,死人骸骨相撑拄。
结发行事君,慊慊心意关。
明知边地苦,贱妾何能久自全?

译文:
放马饮水长城窟,泉水寒冷伤马骨。
找到长城的官吏对他说,“千万别再留滞太原的劳役卒!”
(当官的说:)“官家的工程有期限,快打夯土齐声喊!”
(太原差役说:)“男儿自当格斗死,怎能抑郁造长城?”
长城绵绵无边际,绵延不断三千里。
边城无数服役的青壮年,家乡无数的妻子孤独居。
捎书带信与妻子:“快快重嫁不要等!
嫁后好好伺侯新公婆,时时记住不要忘了我这个旧男人。”
妻子回书到边地,(妻子信中质问:)“你如今说话怎么这么难听?”
(太原差役信中说:)“身陷祸难回不去,为什么还留住人家女儿不放呢?
生下男孩千万不要养,生下女孩用肉来哺。
你难道没有看见长城下,死人的骸骨相交叉?”
(妻子信中说:)“嫁你就该随着你,想来不够牵记你。
明明知道边地苦,我怎能长久活着求自保?”

鉴赏
本诗用乐府旧题,以秦代统治者驱使百姓修筑长城的史实为背景,通过筑城役卒夫妻对话,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,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。诗中用书信往返的对话形式,揭示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彼此间地深深牵挂,赞美了筑城役卒夫妻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。语言简洁生动,真挚感人。
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说“余至长城,其下有泉窟,可饮马,古诗《饮马长城窟行》,信不虚也。”诗的首句着题,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,第二句以“水寒伤马骨”,渲染边地苦寒,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。
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。
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,“慎莫稽留太原卒”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,也透露了“稽留”乃往日常有之事,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“稽留”的迹象,若不如此,岂敢凭空道来。
“官作自有程,举筑谐汝声”这是官吏的回答一派官腔,也话中有话。只此两句,气焰、嘴脸,如在眼前。
那役卒看此情景,听此言语,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: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,怎能这样窝窝囊囊,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!
以上“三层往复之辞,第一层用明点,下二层皆用暗递,为久筑难归立案,文势一顿”。
“长城何连连,连连三千里”。如此“官作”,何时竣工?再加上如此官吏,更是归期无望。也正因这样,才造成“边城多健少,内舍多寡妇”。古时凡妇人独居者,皆可称“寡妇”。
两个“多”字,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。这四句诗,不脱不粘,似是剧中的“旁白”,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,由个别推向一般,由“健少”而连及“内舍”,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。
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,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,对于勾连上下内容,都是很重要的。
“作书与内舍”,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。“便嫁”三句,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。首先劝其“嫁”,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,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,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(即役卒自己)。
第一句,明确果断;二三两句,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,与难忘的情爱。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、必死边地的绝望。藏而不露,亦是为了体贴对方。
“书”中三句,第一句为主,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。所以妻子”报书往边地“,便抓住主旨,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,“今”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。语嗔情坚,其心自见,一语道尽,余皆无须赘言。
“身在”六句,上役卒再次寄书,就自己的“出语”,与妻子的指责,作进一步解释。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,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(指其妻)受苦呢?
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――“生男慎勿举(养育),生女哺(喂食)用脯(干肉)。不见长城下,尸骸相支拄”。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,暗示自己的“祸难”,自己的结局。
因此,前言虽“鄙”,亦出无奈,其情之苦,其心之善,郭不可察,何况其妻呢!妻子也确实理解了,感动了,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。但是纵已以死相许,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,只以“苦”字代之,回肠九曲,又言辞得体。

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、以点为主的手法,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,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,两者相互引发,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“筑怨兴徭九千里”,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,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。
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,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,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,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。
不仅如此,语言也很有特色,役卒对差吏的刚毅、愤慨之词,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、又不得不断的寄语,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,和性格的丰富性;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,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;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,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。
如此“奇作”的出现,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,似乎还应该指出,它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、“人民死丧略尽”的现实的了解,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,那么本诗的现实意义,也是不可忽略的。
-
上一篇: 《道德经》第八十章赏析
-
下一篇: 孔融《与曹公论盛孝章书》的译文与赏析